如何看待当今大学生过年回家认为「自己还是小孩子」的行为?
大家族里的几个大学生孩子回家了,在春节中的相聚,听其言、观其行,发现二十多的高大小伙子们,外表成年,语言也很花哨,时不时飘出来几个英语单词,但是思维、认知、动作依然有孩子的意味,不知道是该悲哀还是该高兴。
这是否为社会通病,还是家族教育的缺失,随手看了一些资料,才看到一些大学生共同的特征,回家巨婴、法律盲童,怪不得一则消息称,许多中国的留学生看到国内同年龄段的大学生,总会轻蔑地说,幼稚。
春节是"返乡巨婴"到"自我降维"的魔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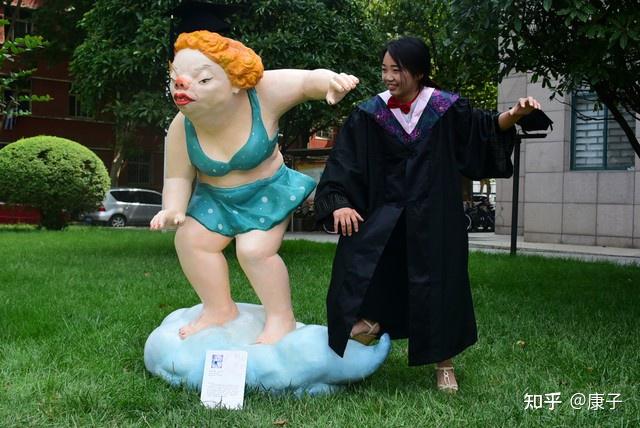
比如2023年除夕夜,上海某三甲医院急诊科接诊了特殊病例:21岁医学生小林因连续三天装睡逃避洗碗,被母亲掀被子时扭伤脚踝。这个荒诞中透着心酸的故事,揭开了一个隐秘的社会症结——68.7%的大学生承认春节回家会不自觉地"行为幼化"(《2024春节代际行为调查报告》)。在法学视野下,这些手持身份证的"法定成年人"上演着分裂戏码:他们能在校园维权群里为宿管断电据理力争,回家却坦然收下塞进睡衣口袋的压岁钱;在历史维度中,这种状态恰似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表面威严的成年礼器,内壁却刻满稚拙的孩童涂鸦。
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何在?一是法律成年与事实成年的时空错位。我国《民法典》规定18岁即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现实中的"成年套餐"却要等到22岁大学毕业才陆续解锁。最高院的案例也表明了,成年大学生向家长讨要大学学费,并未得到判决的支持。
但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需要家长完全资助的,经济的不独立,造就了春节的不独行。

二是婚恋自由需通过"春节见家长"认证,受到传统思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幸福需要门当户对、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的, 大学生的婚姻或者正式的爱情受到家长、家庭的深度影响,缺乏异性配偶的加持,是被当做孩子的最大伪装,即使在大学是海王级别的人物,不带来出席春节的聚餐的异性,难以被家人所认可。
三是经济独立往往始于"工作红包豁免权" 。不上班则有权利领取红包,家长、长辈有义务给其经济资助,这些传统让大学生沉迷于当孩子的幻想中,造成以是否工作标准来论及成年。有红包则未成年,直到丧失资格后,才明白已经长大。
这种制度性措施和社会共同的认知延迟造就了特殊的社会身份缓冲区,就像程序员在代码里设置的debug模式——既不是完全的孩童,也非真正的成人。
这种割裂在春节集中爆发,形成"彼得潘综合症"的温床。

比如母亲仍会自然擦去25岁女儿嘴角的饭粒,父亲坚持替身高180的儿子整理衣领。家庭角色剧本的惯性力量,比抖音算法更精准地推送着"孩童模式"。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今天的"心中贼"恰是:
大学生既渴望独立又贪恋庇护的矛盾;既批判传统又依赖旧序的撕裂;既向往未来又恐惧未知的忐忑 。
要治愈这种集体性"成年未遂症",需要认识到:真正的成年礼不在祠堂,而在每次主动接过母亲手中锅铲的瞬间;不在法律文书,而在坦然说出"爸妈,这次换我来"的勇气里。